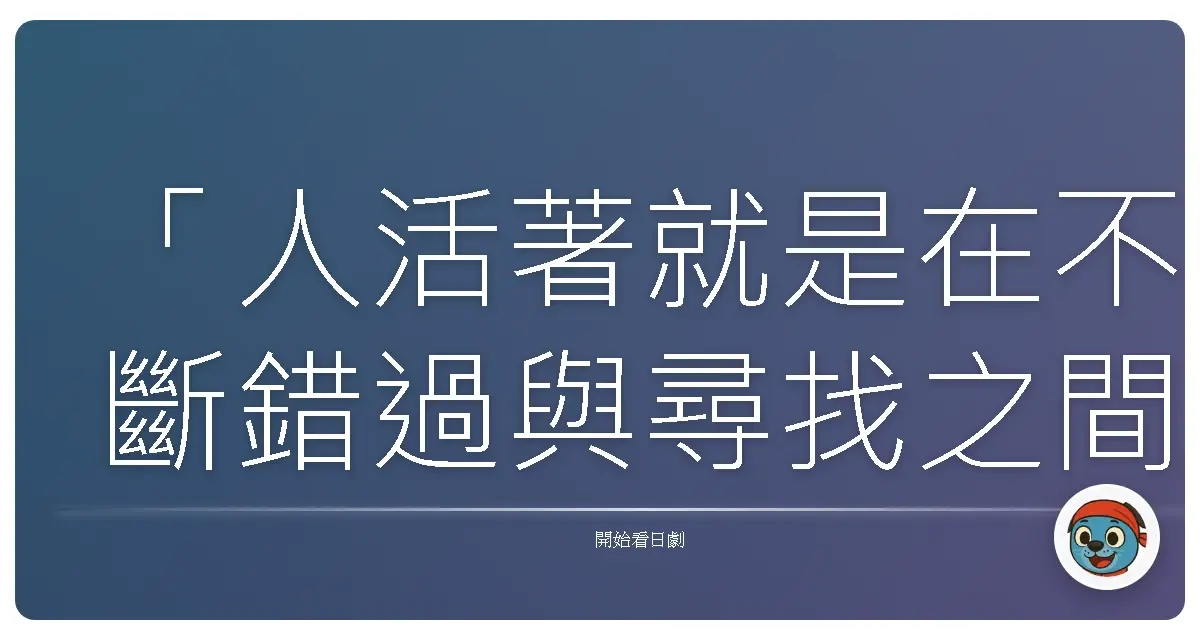
「人活著就是在不斷錯過與尋找之間反覆演奏,有些旋律錯了音,也成了一生的記號。」《四重奏》,2017
如果你問我,人生像不像一首音樂?我會說,當然像。只是那不是一首從頭到尾都順暢和諧的交響樂,而更像是四個人各彈各的調子,在碰撞、對話、錯落與默契之中,慢慢拼湊出一段段旋律。有的時候,你以為只是伴奏,卻成了別人主旋律的核心。有的時候,你練了一輩子的獨奏,最後才發現,沒有和聲,再漂亮也只是孤單的聲音。
《四重奏》這部日劇沒有什麼高潮迭起的大事件,沒有戀愛劇裡那些痛快淋漓的表白,也沒有懸疑片裡的反轉結局。但它用一種極其細膩的方式,把人的脆弱與堅強、熱情與冷漠、現實與夢想拉在一起,像四條弦在同一個琴身上發聲,一下子把我拉回了那些不曾說出口、卻深藏心裡的故事。
我記得那年剛從一段很疲憊的感情關係中抽身出來,整個人像是被抽乾了音色的琴,空有形體,卻什麼都發不出來。朋友推薦我看《四重奏》,我一開始只是抱著殺時間的心情按下播放鍵,沒想到,一集接著一集,那些看似平淡、甚至有點古怪的角色對話,卻像一根根琴弓,撩撥著我最深處的弦。
「大人就是知道不能那樣做,但還是那樣做的人。」這句台詞打中我心裡某個不願面對的角落。年輕時,我們總以為自己可以選擇要成為什麼樣的人。長大以後才明白,人生多半是在不想成為什麼樣的自己中掙扎。那段時間,我一邊工作,一邊偷偷在廁所裡哭。不是為了誰,只是心裡太多想說的話沒人懂,太多想做的事被現實壓住無法動彈。
劇中每個角色都不完美,但也正因為如此,他們的真實才讓我動容。卷和家的料理是療癒的,卻也藏著逃避的味道。別府彷彿什麼都知道,卻也總是在關鍵時刻選擇沉默。家森的嘴賤裡其實藏著一顆害怕被遺棄的心。還有真紀,總是一臉淡定地說出驚人之語,彷彿全世界的誤會與孤獨都與她無關。
有一場戲讓我久久不能釋懷。真紀坐在窗邊,輕聲說:「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這麼孤單。」那句話我來來回回聽了很多次,每次聽都有不同的感覺。年輕時的我以為孤單是被朋友遺忘,是一個人吃飯看電影。後來我才懂,真正的孤單是你身邊圍繞著人,但你說的話他們不懂,你想的事他們不關心。
《四重奏》很少說愛,但全劇每一分每一秒,都讓我感覺到某種無聲的「我在乎你」。不是情人間的甜言蜜語,也不是親情間的理所當然,而是一種介在朋友與陌生人之間的微妙關係。我想起自己最難熬的那段日子,有個朋友總是每天早上傳一則搞笑貼圖來,沒有多餘的問候,也沒有催促我振作起來。只是這樣默默地,每天都傳。我曾經覺得那沒什麼,但當我慢慢好起來後,我知道,那是她給我的一種陪伴,一種像四重奏裡那種你彈你的、我彈我的,但我們終究還是在同一首曲子裡。
四個人住在輕井澤那間小屋裡的模樣,讓我想到曾經和幾個朋友租下一層老公寓,各自一間房,晚上大家窩在客廳吃泡麵看電影。我們都說那只是暫時的過渡期,但那段時間,反而成了我們後來常常回憶的「最好時光」。就像劇裡那句話說的:「不管再怎麼認真演奏,音樂總會結束。那麼,我們至少應該在它結束前,好好地享受它。」
長大後的我們,越來越不敢說「夢想」這兩個字。怕太不切實際,怕被笑,怕失敗。但《四重奏》提醒我,有時候我們還能牽起樂器,有人陪我們錯幾個音,也是一種幸運。夢想不是一定要成功才叫夢想,它也可以是一段你願意走下去的路,即使明知道前方不一定光明。
我有個朋友從小學琴,家人希望她成為演奏家,但她高三那年突然決定不考音樂系。她說她受夠了日復一日的壓力,也不確定自己是否真的愛音樂。多年後,我在一場音樂會上遇見她,她說她現在在教小朋友彈琴,雖然不是當年想像的那種「音樂人生」,但她每天看到孩子們因為彈出第一首曲子而興奮的眼神,就覺得,這樣也挺好。
就像四重奏那群人,沒有成為閃閃發光的樂團,也沒有站上什麼國際舞台,但他們用自己的方式,一點一滴地,把生活過得有聲有色。我們每個人,不也是這樣嗎?不見得要讓世界聽見,但至少在某個深夜裡,對著自己說:「我沒有放棄自己想彈的那首歌。」
《四重奏》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故事,但它像一張陳年的錄音帶,當你心煩的時候放來聽,會突然聽見自己的聲音。那些曾經覺得丟臉的選擇、被看不起的堅持、走錯的路,其實都是我們音符的一部分。不完美,卻誠實。
有一天我問我媽:「你年輕的時候,有沒有什麼夢想沒實現?」她愣了一下,然後笑笑說:「我想學鋼琴啊,結果你阿公說那是有錢人家的玩意兒,學那個沒飯吃。」我那一刻突然心酸起來。也許她這輩子都不會彈琴,但她把所有的愛和溫柔,彈在我們這些孩子身上了。
所以啊,不要小看自己那些沒說出口的小夢想,也不要因為錯過了某些節奏,就覺得自己沒救了。音樂可以重來,人生也可以。我們可以一直彈錯,但只要還有人願意聽,我們就還有再演一次的理由。
最後,我想說,《四重奏》不是給你答案的劇。它只是靜靜地坐在你旁邊,陪你聽完一首又一首人生的練習曲。有時你會想跳過某段旋律,但當你再回頭聽,才發現,那段也許就是你最真的聲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