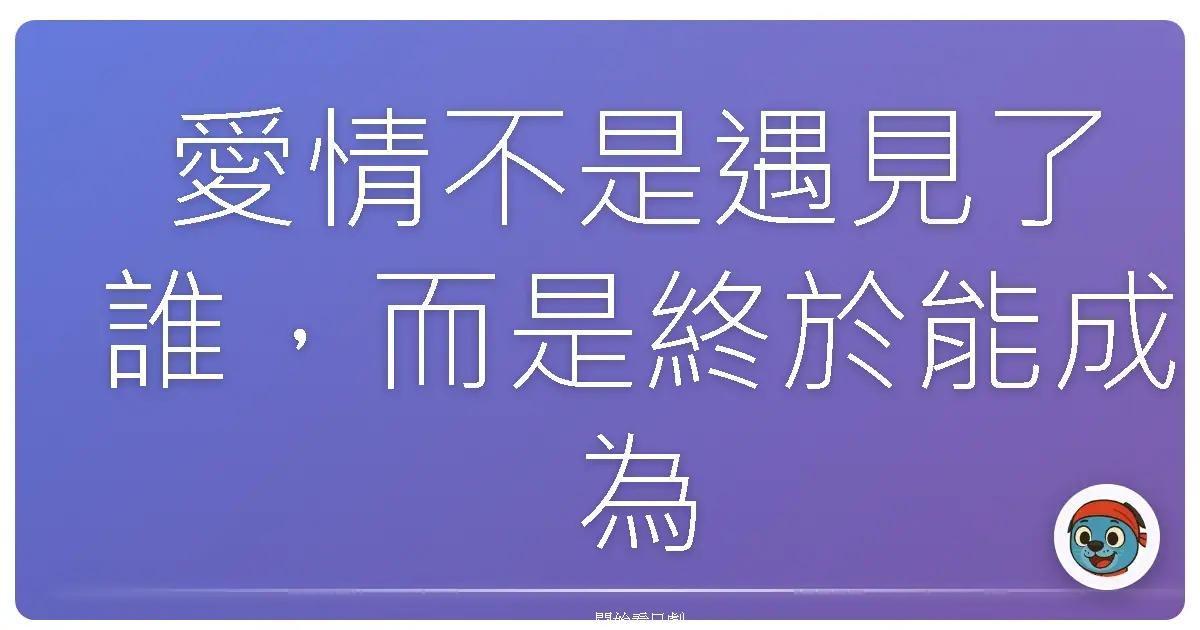
愛情不是遇見了誰,而是終於能成為自己。《初戀 First Love》,2022
有些作品不聲不響地出現,在生命的某個轉角,悄悄叩門。《初戀 First Love》就是這樣的存在。它不曾宣告自己非看不可,也沒有震耳欲聾的配樂或撕心裂肺的演技,有的只是日式敘事裡特有的靜靜溫柔,緩緩疊出一層又一層的情感波動,像雪落在窗沿那樣,無聲但真實。
這部日劇對許多人來說,是浪漫的,是懷舊的,是心碎後重生的慰藉。但對某些人而言,它更像是一面鏡子。映照出當年青澀的期待,成年的遺憾,以及那份始終不敢碰觸卻一直存在的情感。它讓人想起某個冬天的站牌、某首歌的前奏、某張來不及寄出的明信片。不是為了回顧,而是終於有機會對自己承認:那時候,是真的喜歡過;那時候,是真的做不到。
或許每個人一生中,都會經歷幾次「初戀」。不是每次都是人與人的相遇,也可能是第一次真誠地喜歡上一件事、一種生活,甚至是某個夢想。那份無所畏懼、全心投入的熱度,是青春獨有的勇氣。但這份勇氣不會永遠都在。它會因為一次失敗而退縮,也可能在現實的磨耗下逐漸變得不那麼堅定。到最後,我們習慣用「長大」來解釋那些不再追求的理由,用「成熟」來包裝那份其實依然存在的懊悔與放不下。
《初戀 First Love》裡的人物像極了生活裡的我們。他們也曾年少輕狂、也曾為愛低頭;他們也曾拼命追夢、也曾狼狽逃離。他們沒有高光的主角命運,只有一段段走錯又再繞回來的人生路。但就是這樣的平凡,讓人感到真實。彷彿看見了自己多年來小心翼翼收藏在心底的那部分記憶,不被他人理解,卻始終無法放下。
青春是一場奔跑,有人跌倒、有人迷路,也有人從頭到尾沒停下來。但終點在哪裡,從沒人知道。有人以為是事業成功,有人以為是結婚生子,有人則覺得是回到最初的那個夢。但更多時候,人生其實是一個圓。兜兜轉轉之後,我們會發現,所謂「成長」,並不是學會擁有,而是學會放手、學會理解、學會原諒,最重要的,是學會和當年的自己和解。
劇中的音樂,特別是宇多田光那首《First Love》,是一種聲音的回憶。它不僅唱出愛情的模樣,更唱出一段時光、一種心境。每一次旋律響起,彷彿聽見了某個時代的自己在耳邊低語:「那時候,你真的很勇敢。」而這句話,是很多人長大以後,再也不會對自己說的話。因為世界變得太快,變得太重,人們開始害怕承認曾經的自己是那麼純粹。怕別人笑,也怕自己再受傷。
這樣的害怕,其實沒什麼不對。它是經驗的沉澱,也是保護自己的本能。但在某些時刻,例如在深夜獨處、在某段旋律響起時、在回憶湧上的一瞬間,那份久違的情感依然會被喚醒。而那時候的我們,或許才能坦然承認:有些感情,不是結束了,而是被放在心裡另一個地方,等待有一天可以不再痛地拿出來看看。
人生不會像戲劇那樣有明確的高潮和結尾,大多數時候,是一種模糊的延續。今天的我們不是昨天的我們,明天也不會是今天的延伸。但在那些看似無關的斷點之中,總有一些情感會連接著我們不同時期的自己。《初戀 First Love》之所以動人,不是因為它告訴我們一段愛情的走向,而是它讓我們在劇中某個瞬間,終於能對自己說:「原來,我還記得。」
記得那個愛得用力、哭得用力、夢得用力的自己。也記得那些因為太年輕而無法好好說出口的話、做不完的夢、走不到的遠方。那些未完成的故事,在某種意義上,不也是人生的一部分?如果人生只由成功與結果構成,那中間那些努力、那些痛哭、那些轉身,豈不全都白費?但它們沒有白費。因為正是它們,讓我們成為現在的自己。
有一位朋友曾經在失戀後說過這樣一句話:「我不是沒了他過不下去,我只是突然之間,對未來沒有想像了。」這句話後來在心裡停留了很久很久。不是因為多感傷,而是因為太真實。有些人離開的不是生活,而是那份對未來的想像。而重新找回這份想像,往往不是靠另一段感情,不是靠時間,不是靠逃避,而是靠一次次地走回那個夢開始的地方,再一次誠實地問問自己:「我還願意相信嗎?」
初戀這部日劇沒有給出答案,它只是用一種極其溫柔的方式,告訴我們:「曾經的你很好,現在的你也不差。」人生不是要一直向前,也可以偶爾回頭,和自己說一聲:「謝謝你曾經那麼努力地愛過,夢過,痛過。」那些情感不需要被遺忘,也不該被掩蓋,它們只是換了一種方式,成為我們的養分。
很多人說,回不去的才叫初戀。但也許,不是回不去,而是終於學會不再強求回去。因為人生本就該往前走,而不是在原地等待一個從未真正存在的結局。真正重要的,是我們是否從那份初衷中,學會了怎麼去愛、怎麼去成全、怎麼去接納那個最真實的自己。
也許到最後,我們仍會記得某年某月的某個人,記得他說過的一句話、遞過的一杯水、擁抱過的瞬間。但那不再是傷口,而是一種溫柔的證明——證明我們曾經愛過、活過、相信過,也真心期盼過。
這樣就夠了。真的,這樣就夠了。